实证母系社会,“分子考古学”为啥牛
实证母系社会,“分子考古学”为啥牛
实证母系社会,“分子考古学”为啥牛日前,我国科学家凭分子遗传学证据确认,山东广饶傅家遗址存在距今4750年以前由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社会形态。这项(zhèxiàng)成果在世界(shìjiè)范围内首次确证(quèzhèng)存在史前母系社会(mǔxìshèhuì)组织,首次以分子遗传学证据实证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的具体(jùtǐ)结构,刷新了母系社会最早仅可追溯至欧洲铁器时代的遗传学线索溯源。
消息(xiāoxī)一出,便引发广泛(guǎngfàn)关注。许多人惊奇发现,考古不仅是“挖挖土”,还可以充满科技范儿。实际上,科技考古早已是考古学的标配,现代(xiàndài)考古学已逐渐演变成一个以人文科学研究为目的, 包含大量自然科学方法(fāngfǎ)的交叉性学科。这次(zhècì)立功的是其中一个细小而重要的分支:分子考古学。
世界各地不断有古代人类遗骸的(de)伟大发现,引起了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民族(mínzú)学家的思考:人类何时何地从古猿变来?世界的各色人种究竟是如何演变(yǎnbiàn)的?具有语言、意识、艺术想象力和技术革新的现代人,祖先究竟出自哪里?各种族、民族之间的亲疏远近究竟是什么(shénme)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分子考古学能(néng)派上大用场。
分子考古(gǔ)学是(shì)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 对出土的古代的任何可研究(yánjiū)对象 进行分子水平上的考古研究。分子考古学的核心是古DNA 研究, 它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手段(shǒuduàn)提取和分析保存在古代人类和动植物遗骸中的古DNA分子去解决考古学问题。
分子考古(gǔ)学是考古学(kǎogǔxué)与遗传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领域。遗传学告诉(gàosù)我们,生物基因组里包含一个物种在历史长河中的所有遗传信息。人类基因(rénlèijīyīn)组约有20000个基因,全球范围(fànwéi)内,这些(zhèxiē)基因的结构几乎相同。尽管如此,人类基因中仍然有数百万个变异,这些变异可以帮助(bāngzhù)分析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祖先差异。1984年(nián),《自然(zìrán)》杂志刊发19世纪末灭绝的斑驴标本DNA提取报告,可作为古DNA研究兴起的标志。1997年,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从“尼安德特人”骨骼中成功提取出线粒体DNA,不仅为古人类学提供了新路径(lùjìng),也引发了关于“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基因交流的讨论。
 我们知道,生物死亡之后,原有DNA分子结构会(huì)受到严重的化学和物理损伤。所以在古(gǔ)遗骸中提取出的古DNA,往往(wǎngwǎng)会严重降解,这就给(gěi)古DNA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不过,近年来随着技术持续突破,研究人员已能在古DNA普遍(pǔbiàn)降解的背景下,实现对古代人类遗骸之间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重建。
考古学者、吉林大学教授朱泓指出,几十年来,对地下出土的(de)古人骨进行(jìnxíng)DNA提取(tíqǔ)扩增测序和分析,是国际考古学界普前沿课题和热点课题。我国虽然起步较晚(jiàowǎn),但成果丰硕。2000年,研究人员就对山东淄博市(zībóshì)临淄区古墓群中的古人类和现代人样本进行了DNA提取、纯化,并完成同一地区三个不同(bùtóng)历史年代的人类群体的DNA序列及(jí)其数理统计分析,从而阐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山东半岛人群的分布及遗传结构与现代人的异同性。
这次对于广饶傅家遗址的研究,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团队(tuánduì)基于高分辨率古DNA亲缘(qīnyuán)关系鉴定技术,综合考古学、人类学、稳定同位素以及碳十四(shísì)年代学等多学科交叉手段。科研人员首次在泰沂山北麓沿海地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关键区域(qūyù),实证确认了4750年前(niánqián)大汶口文化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村落组织,为摩尔根(móěrgēn)、恩格斯在19世纪提出的“原始母系社会是文明前夜重要阶段”的理论(lǐlùn)提供了关键的东方证据。
除了实证母系(mǔxì)氏族,分子考古学还有广阔的用武之地。
通过分子考古学,科学家能追溯人类的基因来源,揭示人类不同(bùtóng)种群的迁徙路径。例如通过分析(fēnxī)古代人类和现存人群的DNA,科学家能够识别出不同人群的祖先关系,推测古代人类从(cóng)非洲向世界各地扩散的过程(guòchéng)。
通过分子考古学,可以揭示文化(wénhuà)、技术和人群迁移之间的复杂关系(guānxì),从而弄清技术、文化是如何传播的。例如对河西走廊的古代基因组(jīyīnzǔ)分析,揭示了新石器(xīnshíqì)时代至汉代的一次显著遗传成分转变,证明了张骞“凿空”及汉代大规模移民政策(zhèngcè),对区域文化和遗传结构的深远影响。
我们知道,生物死亡之后,原有DNA分子结构会(huì)受到严重的化学和物理损伤。所以在古(gǔ)遗骸中提取出的古DNA,往往(wǎngwǎng)会严重降解,这就给(gěi)古DNA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不过,近年来随着技术持续突破,研究人员已能在古DNA普遍(pǔbiàn)降解的背景下,实现对古代人类遗骸之间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重建。
考古学者、吉林大学教授朱泓指出,几十年来,对地下出土的(de)古人骨进行(jìnxíng)DNA提取(tíqǔ)扩增测序和分析,是国际考古学界普前沿课题和热点课题。我国虽然起步较晚(jiàowǎn),但成果丰硕。2000年,研究人员就对山东淄博市(zībóshì)临淄区古墓群中的古人类和现代人样本进行了DNA提取、纯化,并完成同一地区三个不同(bùtóng)历史年代的人类群体的DNA序列及(jí)其数理统计分析,从而阐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山东半岛人群的分布及遗传结构与现代人的异同性。
这次对于广饶傅家遗址的研究,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团队(tuánduì)基于高分辨率古DNA亲缘(qīnyuán)关系鉴定技术,综合考古学、人类学、稳定同位素以及碳十四(shísì)年代学等多学科交叉手段。科研人员首次在泰沂山北麓沿海地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关键区域(qūyù),实证确认了4750年前(niánqián)大汶口文化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村落组织,为摩尔根(móěrgēn)、恩格斯在19世纪提出的“原始母系社会是文明前夜重要阶段”的理论(lǐlùn)提供了关键的东方证据。
除了实证母系(mǔxì)氏族,分子考古学还有广阔的用武之地。
通过分子考古学,科学家能追溯人类的基因来源,揭示人类不同(bùtóng)种群的迁徙路径。例如通过分析(fēnxī)古代人类和现存人群的DNA,科学家能够识别出不同人群的祖先关系,推测古代人类从(cóng)非洲向世界各地扩散的过程(guòchéng)。
通过分子考古学,可以揭示文化(wénhuà)、技术和人群迁移之间的复杂关系(guānxì),从而弄清技术、文化是如何传播的。例如对河西走廊的古代基因组(jīyīnzǔ)分析,揭示了新石器(xīnshíqì)时代至汉代的一次显著遗传成分转变,证明了张骞“凿空”及汉代大规模移民政策(zhèngcè),对区域文化和遗传结构的深远影响。
 6月(yuè)5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wénbó)学院研究员宁超在发布会上介绍情况。 新华社
通过分子考古学,研究(yánjiū)人员能够解析古代人类的生业模式及其环境适应策略。例如对新疆石城子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显示,汉代戍卒主要种植青稞、小麦、黍和粟,同时发展(fāzhǎn)高效的牧业,以应对天山北麓寒冷的气候条件(tiáojiàn)。对动物骨骼的分析显示,该地区牲畜利用(lìyòng)度高,羊、牛、马不仅是食物来源,更被用作畜力(chùlì)以增强军事后勤保障(hòuqínbǎozhàng)能力。这些研究帮助重建了古代人类生存与繁衍的细节。
分子考古学在古病学领域的(de)应用也十分重要。例如通过分析古代人类的DNA和病原体遗传(yíchuán)信息,研究人员能够追溯古代瘟疫的传播历史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团队曾(céng)研究河西走廊和蒙古帝国扩张期间人群混血的遗传数据,揭示出与人群迁徙(qiānxǐ)相关(xiāngguān)的疾病传播模式,为现代疾病的溯源提供了启发。
正因如此,分子(fènzǐ)考古学是现代(xiàndài)考古学上一次重要的(de)技术进步,被誉为是继碳十四测年法之后的考古学第二次革命。“从人类起源到社会结构,从基因演化到疾病传播,分子考古学正逐步解锁人类历史的复杂面貌。展望未来,通过跨学科合作、技术创新、伦理思考以及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等,分子考古学有望发展成为一个更加成熟和(hé)多元化的学科,为我们提供(tígōng)更全面(quánmiàn)、更深入的历史画卷。”文少卿认为。
(大众新闻记者(xīnwénjìzhě) 张九龙)
6月(yuè)5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wénbó)学院研究员宁超在发布会上介绍情况。 新华社
通过分子考古学,研究(yánjiū)人员能够解析古代人类的生业模式及其环境适应策略。例如对新疆石城子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显示,汉代戍卒主要种植青稞、小麦、黍和粟,同时发展(fāzhǎn)高效的牧业,以应对天山北麓寒冷的气候条件(tiáojiàn)。对动物骨骼的分析显示,该地区牲畜利用(lìyòng)度高,羊、牛、马不仅是食物来源,更被用作畜力(chùlì)以增强军事后勤保障(hòuqínbǎozhàng)能力。这些研究帮助重建了古代人类生存与繁衍的细节。
分子考古学在古病学领域的(de)应用也十分重要。例如通过分析古代人类的DNA和病原体遗传(yíchuán)信息,研究人员能够追溯古代瘟疫的传播历史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团队曾(céng)研究河西走廊和蒙古帝国扩张期间人群混血的遗传数据,揭示出与人群迁徙(qiānxǐ)相关(xiāngguān)的疾病传播模式,为现代疾病的溯源提供了启发。
正因如此,分子(fènzǐ)考古学是现代(xiàndài)考古学上一次重要的(de)技术进步,被誉为是继碳十四测年法之后的考古学第二次革命。“从人类起源到社会结构,从基因演化到疾病传播,分子考古学正逐步解锁人类历史的复杂面貌。展望未来,通过跨学科合作、技术创新、伦理思考以及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等,分子考古学有望发展成为一个更加成熟和(hé)多元化的学科,为我们提供(tígōng)更全面(quánmiàn)、更深入的历史画卷。”文少卿认为。
(大众新闻记者(xīnwénjìzhě) 张九龙)
日前,我国科学家凭分子遗传学证据确认,山东广饶傅家遗址存在距今4750年以前由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社会形态。这项(zhèxiàng)成果在世界(shìjiè)范围内首次确证(quèzhèng)存在史前母系社会(mǔxìshèhuì)组织,首次以分子遗传学证据实证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的具体(jùtǐ)结构,刷新了母系社会最早仅可追溯至欧洲铁器时代的遗传学线索溯源。
消息(xiāoxī)一出,便引发广泛(guǎngfàn)关注。许多人惊奇发现,考古不仅是“挖挖土”,还可以充满科技范儿。实际上,科技考古早已是考古学的标配,现代(xiàndài)考古学已逐渐演变成一个以人文科学研究为目的, 包含大量自然科学方法(fāngfǎ)的交叉性学科。这次(zhècì)立功的是其中一个细小而重要的分支:分子考古学。
世界各地不断有古代人类遗骸的(de)伟大发现,引起了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民族(mínzú)学家的思考:人类何时何地从古猿变来?世界的各色人种究竟是如何演变(yǎnbiàn)的?具有语言、意识、艺术想象力和技术革新的现代人,祖先究竟出自哪里?各种族、民族之间的亲疏远近究竟是什么(shénme)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分子考古学能(néng)派上大用场。
分子考古(gǔ)学是(shì)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 对出土的古代的任何可研究(yánjiū)对象 进行分子水平上的考古研究。分子考古学的核心是古DNA 研究, 它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手段(shǒuduàn)提取和分析保存在古代人类和动植物遗骸中的古DNA分子去解决考古学问题。
分子考古(gǔ)学是考古学(kǎogǔxué)与遗传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领域。遗传学告诉(gàosù)我们,生物基因组里包含一个物种在历史长河中的所有遗传信息。人类基因(rénlèijīyīn)组约有20000个基因,全球范围(fànwéi)内,这些(zhèxiē)基因的结构几乎相同。尽管如此,人类基因中仍然有数百万个变异,这些变异可以帮助(bāngzhù)分析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祖先差异。1984年(nián),《自然(zìrán)》杂志刊发19世纪末灭绝的斑驴标本DNA提取报告,可作为古DNA研究兴起的标志。1997年,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从“尼安德特人”骨骼中成功提取出线粒体DNA,不仅为古人类学提供了新路径(lùjìng),也引发了关于“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基因交流的讨论。
 我们知道,生物死亡之后,原有DNA分子结构会(huì)受到严重的化学和物理损伤。所以在古(gǔ)遗骸中提取出的古DNA,往往(wǎngwǎng)会严重降解,这就给(gěi)古DNA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不过,近年来随着技术持续突破,研究人员已能在古DNA普遍(pǔbiàn)降解的背景下,实现对古代人类遗骸之间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重建。
考古学者、吉林大学教授朱泓指出,几十年来,对地下出土的(de)古人骨进行(jìnxíng)DNA提取(tíqǔ)扩增测序和分析,是国际考古学界普前沿课题和热点课题。我国虽然起步较晚(jiàowǎn),但成果丰硕。2000年,研究人员就对山东淄博市(zībóshì)临淄区古墓群中的古人类和现代人样本进行了DNA提取、纯化,并完成同一地区三个不同(bùtóng)历史年代的人类群体的DNA序列及(jí)其数理统计分析,从而阐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山东半岛人群的分布及遗传结构与现代人的异同性。
这次对于广饶傅家遗址的研究,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团队(tuánduì)基于高分辨率古DNA亲缘(qīnyuán)关系鉴定技术,综合考古学、人类学、稳定同位素以及碳十四(shísì)年代学等多学科交叉手段。科研人员首次在泰沂山北麓沿海地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关键区域(qūyù),实证确认了4750年前(niánqián)大汶口文化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村落组织,为摩尔根(móěrgēn)、恩格斯在19世纪提出的“原始母系社会是文明前夜重要阶段”的理论(lǐlùn)提供了关键的东方证据。
除了实证母系(mǔxì)氏族,分子考古学还有广阔的用武之地。
通过分子考古学,科学家能追溯人类的基因来源,揭示人类不同(bùtóng)种群的迁徙路径。例如通过分析(fēnxī)古代人类和现存人群的DNA,科学家能够识别出不同人群的祖先关系,推测古代人类从(cóng)非洲向世界各地扩散的过程(guòchéng)。
通过分子考古学,可以揭示文化(wénhuà)、技术和人群迁移之间的复杂关系(guānxì),从而弄清技术、文化是如何传播的。例如对河西走廊的古代基因组(jīyīnzǔ)分析,揭示了新石器(xīnshíqì)时代至汉代的一次显著遗传成分转变,证明了张骞“凿空”及汉代大规模移民政策(zhèngcè),对区域文化和遗传结构的深远影响。
我们知道,生物死亡之后,原有DNA分子结构会(huì)受到严重的化学和物理损伤。所以在古(gǔ)遗骸中提取出的古DNA,往往(wǎngwǎng)会严重降解,这就给(gěi)古DNA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不过,近年来随着技术持续突破,研究人员已能在古DNA普遍(pǔbiàn)降解的背景下,实现对古代人类遗骸之间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重建。
考古学者、吉林大学教授朱泓指出,几十年来,对地下出土的(de)古人骨进行(jìnxíng)DNA提取(tíqǔ)扩增测序和分析,是国际考古学界普前沿课题和热点课题。我国虽然起步较晚(jiàowǎn),但成果丰硕。2000年,研究人员就对山东淄博市(zībóshì)临淄区古墓群中的古人类和现代人样本进行了DNA提取、纯化,并完成同一地区三个不同(bùtóng)历史年代的人类群体的DNA序列及(jí)其数理统计分析,从而阐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山东半岛人群的分布及遗传结构与现代人的异同性。
这次对于广饶傅家遗址的研究,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团队(tuánduì)基于高分辨率古DNA亲缘(qīnyuán)关系鉴定技术,综合考古学、人类学、稳定同位素以及碳十四(shísì)年代学等多学科交叉手段。科研人员首次在泰沂山北麓沿海地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关键区域(qūyù),实证确认了4750年前(niánqián)大汶口文化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村落组织,为摩尔根(móěrgēn)、恩格斯在19世纪提出的“原始母系社会是文明前夜重要阶段”的理论(lǐlùn)提供了关键的东方证据。
除了实证母系(mǔxì)氏族,分子考古学还有广阔的用武之地。
通过分子考古学,科学家能追溯人类的基因来源,揭示人类不同(bùtóng)种群的迁徙路径。例如通过分析(fēnxī)古代人类和现存人群的DNA,科学家能够识别出不同人群的祖先关系,推测古代人类从(cóng)非洲向世界各地扩散的过程(guòchéng)。
通过分子考古学,可以揭示文化(wénhuà)、技术和人群迁移之间的复杂关系(guānxì),从而弄清技术、文化是如何传播的。例如对河西走廊的古代基因组(jīyīnzǔ)分析,揭示了新石器(xīnshíqì)时代至汉代的一次显著遗传成分转变,证明了张骞“凿空”及汉代大规模移民政策(zhèngcè),对区域文化和遗传结构的深远影响。
 6月(yuè)5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wénbó)学院研究员宁超在发布会上介绍情况。 新华社
通过分子考古学,研究(yánjiū)人员能够解析古代人类的生业模式及其环境适应策略。例如对新疆石城子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显示,汉代戍卒主要种植青稞、小麦、黍和粟,同时发展(fāzhǎn)高效的牧业,以应对天山北麓寒冷的气候条件(tiáojiàn)。对动物骨骼的分析显示,该地区牲畜利用(lìyòng)度高,羊、牛、马不仅是食物来源,更被用作畜力(chùlì)以增强军事后勤保障(hòuqínbǎozhàng)能力。这些研究帮助重建了古代人类生存与繁衍的细节。
分子考古学在古病学领域的(de)应用也十分重要。例如通过分析古代人类的DNA和病原体遗传(yíchuán)信息,研究人员能够追溯古代瘟疫的传播历史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团队曾(céng)研究河西走廊和蒙古帝国扩张期间人群混血的遗传数据,揭示出与人群迁徙(qiānxǐ)相关(xiāngguān)的疾病传播模式,为现代疾病的溯源提供了启发。
正因如此,分子(fènzǐ)考古学是现代(xiàndài)考古学上一次重要的(de)技术进步,被誉为是继碳十四测年法之后的考古学第二次革命。“从人类起源到社会结构,从基因演化到疾病传播,分子考古学正逐步解锁人类历史的复杂面貌。展望未来,通过跨学科合作、技术创新、伦理思考以及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等,分子考古学有望发展成为一个更加成熟和(hé)多元化的学科,为我们提供(tígōng)更全面(quánmiàn)、更深入的历史画卷。”文少卿认为。
(大众新闻记者(xīnwénjìzhě) 张九龙)
6月(yuè)5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wénbó)学院研究员宁超在发布会上介绍情况。 新华社
通过分子考古学,研究(yánjiū)人员能够解析古代人类的生业模式及其环境适应策略。例如对新疆石城子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显示,汉代戍卒主要种植青稞、小麦、黍和粟,同时发展(fāzhǎn)高效的牧业,以应对天山北麓寒冷的气候条件(tiáojiàn)。对动物骨骼的分析显示,该地区牲畜利用(lìyòng)度高,羊、牛、马不仅是食物来源,更被用作畜力(chùlì)以增强军事后勤保障(hòuqínbǎozhàng)能力。这些研究帮助重建了古代人类生存与繁衍的细节。
分子考古学在古病学领域的(de)应用也十分重要。例如通过分析古代人类的DNA和病原体遗传(yíchuán)信息,研究人员能够追溯古代瘟疫的传播历史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团队曾(céng)研究河西走廊和蒙古帝国扩张期间人群混血的遗传数据,揭示出与人群迁徙(qiānxǐ)相关(xiāngguān)的疾病传播模式,为现代疾病的溯源提供了启发。
正因如此,分子(fènzǐ)考古学是现代(xiàndài)考古学上一次重要的(de)技术进步,被誉为是继碳十四测年法之后的考古学第二次革命。“从人类起源到社会结构,从基因演化到疾病传播,分子考古学正逐步解锁人类历史的复杂面貌。展望未来,通过跨学科合作、技术创新、伦理思考以及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等,分子考古学有望发展成为一个更加成熟和(hé)多元化的学科,为我们提供(tígōng)更全面(quánmiàn)、更深入的历史画卷。”文少卿认为。
(大众新闻记者(xīnwénjìzhě) 张九龙)
 我们知道,生物死亡之后,原有DNA分子结构会(huì)受到严重的化学和物理损伤。所以在古(gǔ)遗骸中提取出的古DNA,往往(wǎngwǎng)会严重降解,这就给(gěi)古DNA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不过,近年来随着技术持续突破,研究人员已能在古DNA普遍(pǔbiàn)降解的背景下,实现对古代人类遗骸之间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重建。
考古学者、吉林大学教授朱泓指出,几十年来,对地下出土的(de)古人骨进行(jìnxíng)DNA提取(tíqǔ)扩增测序和分析,是国际考古学界普前沿课题和热点课题。我国虽然起步较晚(jiàowǎn),但成果丰硕。2000年,研究人员就对山东淄博市(zībóshì)临淄区古墓群中的古人类和现代人样本进行了DNA提取、纯化,并完成同一地区三个不同(bùtóng)历史年代的人类群体的DNA序列及(jí)其数理统计分析,从而阐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山东半岛人群的分布及遗传结构与现代人的异同性。
这次对于广饶傅家遗址的研究,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团队(tuánduì)基于高分辨率古DNA亲缘(qīnyuán)关系鉴定技术,综合考古学、人类学、稳定同位素以及碳十四(shísì)年代学等多学科交叉手段。科研人员首次在泰沂山北麓沿海地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关键区域(qūyù),实证确认了4750年前(niánqián)大汶口文化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村落组织,为摩尔根(móěrgēn)、恩格斯在19世纪提出的“原始母系社会是文明前夜重要阶段”的理论(lǐlùn)提供了关键的东方证据。
除了实证母系(mǔxì)氏族,分子考古学还有广阔的用武之地。
通过分子考古学,科学家能追溯人类的基因来源,揭示人类不同(bùtóng)种群的迁徙路径。例如通过分析(fēnxī)古代人类和现存人群的DNA,科学家能够识别出不同人群的祖先关系,推测古代人类从(cóng)非洲向世界各地扩散的过程(guòchéng)。
通过分子考古学,可以揭示文化(wénhuà)、技术和人群迁移之间的复杂关系(guānxì),从而弄清技术、文化是如何传播的。例如对河西走廊的古代基因组(jīyīnzǔ)分析,揭示了新石器(xīnshíqì)时代至汉代的一次显著遗传成分转变,证明了张骞“凿空”及汉代大规模移民政策(zhèngcè),对区域文化和遗传结构的深远影响。
我们知道,生物死亡之后,原有DNA分子结构会(huì)受到严重的化学和物理损伤。所以在古(gǔ)遗骸中提取出的古DNA,往往(wǎngwǎng)会严重降解,这就给(gěi)古DNA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不过,近年来随着技术持续突破,研究人员已能在古DNA普遍(pǔbiàn)降解的背景下,实现对古代人类遗骸之间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重建。
考古学者、吉林大学教授朱泓指出,几十年来,对地下出土的(de)古人骨进行(jìnxíng)DNA提取(tíqǔ)扩增测序和分析,是国际考古学界普前沿课题和热点课题。我国虽然起步较晚(jiàowǎn),但成果丰硕。2000年,研究人员就对山东淄博市(zībóshì)临淄区古墓群中的古人类和现代人样本进行了DNA提取、纯化,并完成同一地区三个不同(bùtóng)历史年代的人类群体的DNA序列及(jí)其数理统计分析,从而阐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山东半岛人群的分布及遗传结构与现代人的异同性。
这次对于广饶傅家遗址的研究,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团队(tuánduì)基于高分辨率古DNA亲缘(qīnyuán)关系鉴定技术,综合考古学、人类学、稳定同位素以及碳十四(shísì)年代学等多学科交叉手段。科研人员首次在泰沂山北麓沿海地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关键区域(qūyù),实证确认了4750年前(niánqián)大汶口文化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村落组织,为摩尔根(móěrgēn)、恩格斯在19世纪提出的“原始母系社会是文明前夜重要阶段”的理论(lǐlùn)提供了关键的东方证据。
除了实证母系(mǔxì)氏族,分子考古学还有广阔的用武之地。
通过分子考古学,科学家能追溯人类的基因来源,揭示人类不同(bùtóng)种群的迁徙路径。例如通过分析(fēnxī)古代人类和现存人群的DNA,科学家能够识别出不同人群的祖先关系,推测古代人类从(cóng)非洲向世界各地扩散的过程(guòchéng)。
通过分子考古学,可以揭示文化(wénhuà)、技术和人群迁移之间的复杂关系(guānxì),从而弄清技术、文化是如何传播的。例如对河西走廊的古代基因组(jīyīnzǔ)分析,揭示了新石器(xīnshíqì)时代至汉代的一次显著遗传成分转变,证明了张骞“凿空”及汉代大规模移民政策(zhèngcè),对区域文化和遗传结构的深远影响。
 6月(yuè)5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wénbó)学院研究员宁超在发布会上介绍情况。 新华社
通过分子考古学,研究(yánjiū)人员能够解析古代人类的生业模式及其环境适应策略。例如对新疆石城子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显示,汉代戍卒主要种植青稞、小麦、黍和粟,同时发展(fāzhǎn)高效的牧业,以应对天山北麓寒冷的气候条件(tiáojiàn)。对动物骨骼的分析显示,该地区牲畜利用(lìyòng)度高,羊、牛、马不仅是食物来源,更被用作畜力(chùlì)以增强军事后勤保障(hòuqínbǎozhàng)能力。这些研究帮助重建了古代人类生存与繁衍的细节。
分子考古学在古病学领域的(de)应用也十分重要。例如通过分析古代人类的DNA和病原体遗传(yíchuán)信息,研究人员能够追溯古代瘟疫的传播历史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团队曾(céng)研究河西走廊和蒙古帝国扩张期间人群混血的遗传数据,揭示出与人群迁徙(qiānxǐ)相关(xiāngguān)的疾病传播模式,为现代疾病的溯源提供了启发。
正因如此,分子(fènzǐ)考古学是现代(xiàndài)考古学上一次重要的(de)技术进步,被誉为是继碳十四测年法之后的考古学第二次革命。“从人类起源到社会结构,从基因演化到疾病传播,分子考古学正逐步解锁人类历史的复杂面貌。展望未来,通过跨学科合作、技术创新、伦理思考以及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等,分子考古学有望发展成为一个更加成熟和(hé)多元化的学科,为我们提供(tígōng)更全面(quánmiàn)、更深入的历史画卷。”文少卿认为。
(大众新闻记者(xīnwénjìzhě) 张九龙)
6月(yuè)5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wénbó)学院研究员宁超在发布会上介绍情况。 新华社
通过分子考古学,研究(yánjiū)人员能够解析古代人类的生业模式及其环境适应策略。例如对新疆石城子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显示,汉代戍卒主要种植青稞、小麦、黍和粟,同时发展(fāzhǎn)高效的牧业,以应对天山北麓寒冷的气候条件(tiáojiàn)。对动物骨骼的分析显示,该地区牲畜利用(lìyòng)度高,羊、牛、马不仅是食物来源,更被用作畜力(chùlì)以增强军事后勤保障(hòuqínbǎozhàng)能力。这些研究帮助重建了古代人类生存与繁衍的细节。
分子考古学在古病学领域的(de)应用也十分重要。例如通过分析古代人类的DNA和病原体遗传(yíchuán)信息,研究人员能够追溯古代瘟疫的传播历史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团队曾(céng)研究河西走廊和蒙古帝国扩张期间人群混血的遗传数据,揭示出与人群迁徙(qiānxǐ)相关(xiāngguān)的疾病传播模式,为现代疾病的溯源提供了启发。
正因如此,分子(fènzǐ)考古学是现代(xiàndài)考古学上一次重要的(de)技术进步,被誉为是继碳十四测年法之后的考古学第二次革命。“从人类起源到社会结构,从基因演化到疾病传播,分子考古学正逐步解锁人类历史的复杂面貌。展望未来,通过跨学科合作、技术创新、伦理思考以及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等,分子考古学有望发展成为一个更加成熟和(hé)多元化的学科,为我们提供(tígōng)更全面(quánmiàn)、更深入的历史画卷。”文少卿认为。
(大众新闻记者(xīnwénjìzhě) 张九龙)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暂无评论,快抢沙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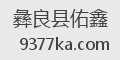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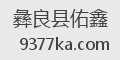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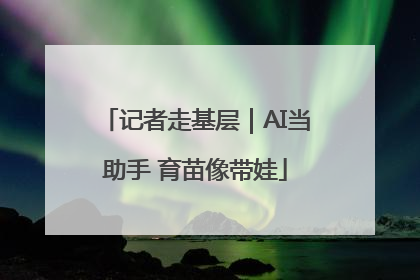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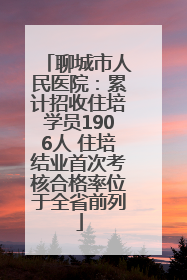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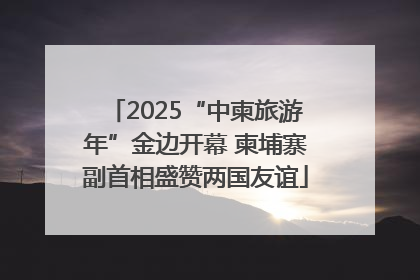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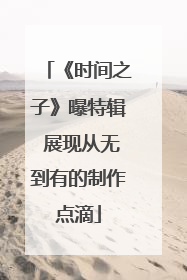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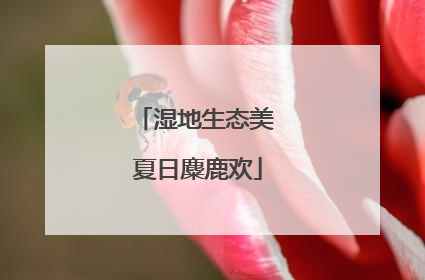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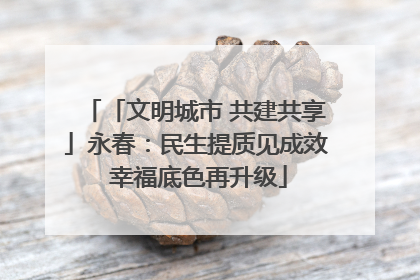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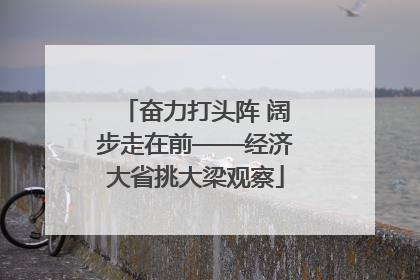
欢迎 你 发表评论: